苏锡嘉:闲话诗歌之外的那些事
读诗作诗,似乎是这个看图刷视频的时代日渐离我们远去的“古早”艺文方式。但好的诗词“言有尽而意无穷”,自有难以取代的表达意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苏锡嘉,得闲时喜欢翻阅诗作,随笔一篇聊聊与诗有关的野史趣闻,为这个夏日添一份诗情意趣的诙谐。

中国是诗的国度,历朝历代,伟大和不伟大的诗人多如天上的繁星,诗作、诗论、诗话汗牛充栋,良莠不齐。读诗的人各有所好,屈原、“李杜”、“元白”、“苏辛”各有自己的拥趸,容不得别人说半句不中听的话。像我这种没有立场、得闲随便翻翻看看的,诗没读懂几首,与诗有关的趣闻倒是关注了不少。今天不谈诗(不是不想谈,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底气谈),八卦一点,我们来聊聊与诗有关的趣事。
01
好诗与坏诗
英国人阿瑟·韦利(1889—1966)以译汉诗成名,他精通古汉语,在欧美汉学界广受推崇。虽然屡被邀请访华,但他从未到过中国,理由是:“我认识的中国人都在唐朝宋朝,我来中国能做什么?”韦利虽然以汉诗权威闻名,但他对汉诗的见解却被钱钟书讥评为“妄欲别裁,多暗中摸索语,可入《群盲评古图》者也”。
但钱对韦利“欲观恶诗,须阅《随园诗话》”的断语十分认同,认为“自有谈艺以来,称引无如随园此书之滥者”(钱钟书《谈艺录》卷五十九)。为证明随园引诗的不堪,钱特以书中介绍的青田才女柯锦机的五言绝句《调郎》为例,认为此诗“极粪土之汙”。
照理,写到这里,为证明自己的说法合理,钱应该把原诗晒出来让大家都看看。结果,一个字也没有出现,也许是钱钟书认为此诗汙到连引用一下都会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我没有钱先生的洁癖,不妨把原诗找出来看看到底汙到什么程度。
柯锦机《调郎》
午夜剔银灯,兰房私事急。
薰莸郎不知,故故偎依立。
小两口闺房之中如厕的事,原不宜喧之于口,亦有点不雅,但以今人的眼光看好像还算含蓄,至少不算“秽作”。相比某些现代诗,甚至还算得上体面。比如,我们来看看当代诗人贾浅浅(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公子)的诗《雪天》:
我们一起去尿尿,
你,尿了一条线,
我,尿了一个坑!
再看《朗朗》: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
当然,以这两首诗来判断贾浅浅的品位显然过于武断,对作者不公平。毕竟,她有好多正经也出彩的诗作,这两首并不能代表她的全貌。但仅以这两首诗而言,对比之下我觉得柯锦机怎么说也还算含蓄,稍显斯文。
一首好诗,多少年后读起来还是会令人击节赞叹。然而,好诗的形成过程却可能一波三折,痛苦不堪。许多诗人说起来都是刻骨铭心般的体验:“一更更尽到三更,吟破离心句不成”(唐·杜荀鹤);“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杜甫);“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六十馀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宋·陆游)。
让诗人寝食不安的往往就是在诗句中找不到一个妥帖的字。有一次苏东坡与苏小妹、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一起论诗。苏小妹说,“轻风细柳,澹月梅花”这两句,中间要加个字作‘腰’,成五言联句,你们觉得该加哪个字?苏东坡说:“轻风摇细柳,澹月映梅花。”苏小妹说:不错,但非最佳(“佳矣,未也”)。黄庭坚说:“轻风舞细柳,澹月隐梅花。”苏小妹仍然觉得虽不错但还不是最好(“佳矣,犹未也”)。二人便问:你的答案是什么?答曰:“轻风扶细柳,澹月失梅花。”苏黄两位大诗人听罢,心服口服(二人抚掌称善)。(清·褚人获《坚瓠集》)
北宋文人陈从易有一次偶然得到一本残破的杜甫诗集,其中文字多有脱落。《送蔡都尉》有“身轻一鸟”句,最后一个字脱落。陈与几个客人开动脑筋,试着补上一字。有说“疾”,有说“落”,有说“起”,有说“下”,难以定夺。后来找到杜诗旧刻本,原句却是“身轻一鸟过”。陈深深叹服:“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会作诗有时能带来官运,这或许是诗人的意外收获。宋时,武毅公曹翰平江南后侍卫京中数年而未能升官。有一天参加宫中宴会,侍臣皆奉命赋诗,唯有曹翰因是武官而未能参与。他便要求说:臣年少时也学过诗,请让我也应诏赋诗。宋太宗说:你是武官,就以刀字为韵吧。曹翰便赋诗寄意说:“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见蟠花旧战袍。”
一个武将能写出这么中规中矩又刚健有力的诗,实属不易。太宗由此连续给他升了几次官。(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引自轻言《历代诗话小品》)

嫌某人的诗不好,最损的评价是什么?东晋名将桓温小时候与殷浩要好。殷浩曾把自己写的诗拿给桓温看,桓温读完把诗收好,然后说:你以后千万不要惹着我了,如果惹我急了就把你的诗拿给别人看。自己写的诗竟然成了别人手里的把柄,这样的诗不写也罢。(宋·惠洪《冷斋夜话》,引自轻言《历代诗话小品》)
有人素不喜欢东坡诗,朋友举东坡绝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如此好诗你怎么能说不好?那人愤然回答道:“鹅也先知,怎么能只说鸭先知?”抬杠到这种地步,对诗人的喜恶真没道理可讲。
吹毛求疵、苛求诗人的近代也有。据说某人写诗,诗中有一句“一轮明月照姑苏”,有人恶评道:“一轮明月何以独照姑苏?应该是‘一轮明月照苏州、无锡等地’方为周全。”
民国时有沈姓人士,为两江、两广督抚沈葆桢的曾孙,能诗善画。作诗常以“陈后山(即宋朝著名诗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第二”自居。有人读了他的诗后恭维他说:“神似陆放翁(即陆游),佳作也。”
沈勃然大怒曰:“放翁是什么东西,吾岂能仿之耶。”(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狂妄到这个地步,却是一首诗也没有流传下来。还好,陈巨来笔下留情,把他的大名隐去了。
02
名人作诗的逸闻轶事
若论产量最高的诗人,乾隆应该有机会问鼎这个桂冠。计入《四库全书》的就有三万三千九百四十首。虽然群臣恭维,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传颂于民间、流传于后世。乾隆对自己诗作的淡而无味、不入品流应该不是完全没有自知之明的。
据《春明梦录》(清·何刚德)记载,乾隆下江南时曾到访白龙寺,纪昀(字晓岚,谥号文达)随侍左右。到白龙寺时正鸣钟,乾隆手痒,伸纸作诗,才写了“白龙寺里撞金钟”七字,纪晓岚便大笑。乾隆闻笑不免大怒,说:“朕诗虽不佳,汝亦岂能当面大笑?”
皇上嘴里说出这样的怒责重话,纪晓岚如答不好,轻则丢官,重则性命难保。还好,纪晓岚应对得当,说:“臣非敢笑也。特因古人诗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一句,积年苦不能对。今观御制七字,恰是天然对偶,不觉喜而失笑耳。”有急智如此,难怪可以完美逃过一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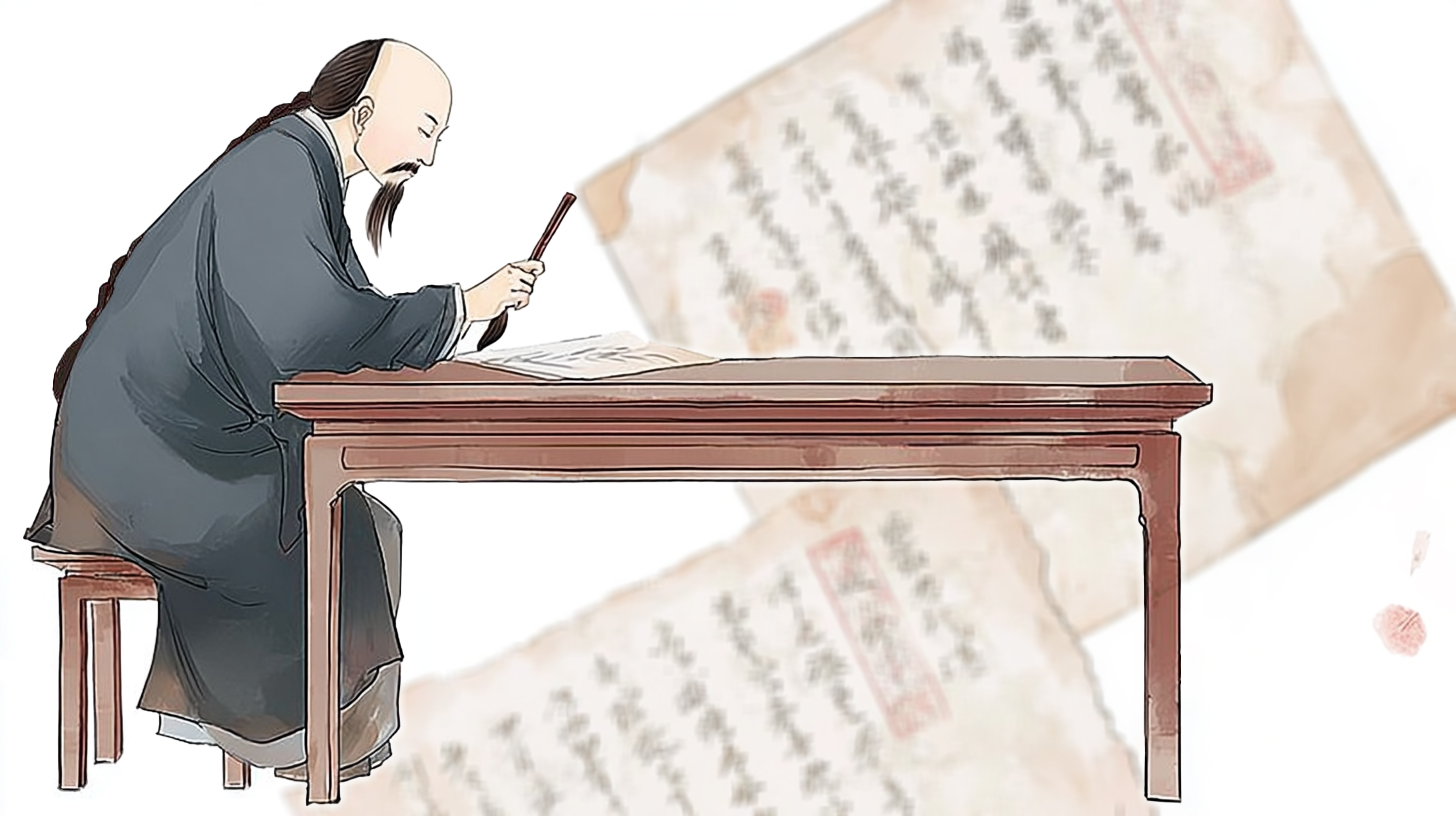
坏人能写出好诗吗?一般人都会很自然地以为人品好,诗品才会好。其实大不然。汪精卫和梁鸿志(字众异)都是世人皆知的大汉奸,却都是当时诗界公认的作诗高手。尤其是汪精卫,他的《双照楼诗词稿》里有不少诗作广受好评,陈寅恪、钱钟书都是眼界很高的大家,却不约而同地对汪的诗作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如“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钱钟书《题某氏集》),“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陈寅恪《阜昌》)。
汪的某些诗一度甚至到了举国传颂的地步,如汪精卫的《被逮口占》之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四:“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他的《狱中杂感》中更有“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豪言。读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当时清廷把汪问斩,我们的历史肯定会多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奈何,命运就是这般捉弄人!
汉奸梁鸿志的诗名似更在汪精卫之上。抗战结束后梁被捕入狱,百无聊赖中仍作诗自遣。但人在狱中,手边已无诗韵可查,只能步旧韵或和前朝人之韵,就这样在狱中还写了不少诗。行刑前还密托人带出监狱,交家人妥为保藏,家人不敢保留,付之一炬。据看过手稿的陈巨来说,内有七首七绝,题为《七无诗》,咏狱内无灯、无凳、无筷、无裤带等状况。
有时,诗人率性而作的一首诗,可能对当事人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坊间谣传事变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不理关外发来的告急电报,以致沈阳失陷,东北沦亡。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激愤之下写了题为《哀沈阳》的两首诗,轰动全国。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半夜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读来琅琅上口,很快便传遍大江南北,不仅张学良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诗中提到的三位女性也立刻成为大众憎恨的对象。
可惜,马君武写诗依据的仅仅是道听途说的传言,诗中的描写与事实完全不符。诗中提到的三个女性——赵四、朱五和胡蝶都实有其人。但除了赵四小姐与张相伴左右外,其他两位名女人(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时期的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胡蝶是当时最红的女明星)都与张学良并无往来,且事发当日人都不在北京。
以讹传讹的一组诗,让朱、胡二人,尤其是胡蝶,饱受舆论轰炸,甚至受到炸弹威胁。
其实,马君武虽然这两首诗写得实在不靠谱,但他本人却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早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因参加同盟会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德国,在柏林大学学冶金,得工科博士学位,是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得到工科博士学位的。
马还精通日、英、德、法文,编撰了《德华字典》,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中国新诗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任广西大学校长时,不论文科、理科还是工科,哪一位教授请假,他都可以代课。请问,今天哪一位校长有这个本事?
03
用统计学研诗之高低
唐诗宋词是中国诗词文学的巅峰,伟大的诗人接踵而至,伟大的作品让人目不暇接。问题随之而来:到底谁更伟大?
国人向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意思是文章的好坏全凭个人喜好,而每个人的喜好各不相同,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比如,李白和杜甫是唐诗的两座丰碑,各有自己的风格和成就,也各有自己的崇拜者,后世学人因此而分成了“扬李抑杜”和“扬杜抑李”泾渭分明的两派。
明人王世贞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他是崇杜的。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是高调的“扬李抑杜”,扬到有点强词夺理。比如,一般人都认为李白嗜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郭沫若却说“杜甫嗜酒实不亚于李白”。依据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统计,杜甫存世的诗和文有1400多首,说到饮酒的有300首,占21%强。而李白的诗和文有1050首,说到饮酒的仅170首,占16%。郭认为虽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杜甫更嗜酒,但两人在爱喝酒这件事上不相上下应该离事实不远。
即使都喜欢李或杜,见解也可能大相径庭,各不相让之下脸红耳赤是难免的。清朝文人钱载(号萚石)和翁方纲(号覃谿),“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必不合,甚至继而相搏”。钱钟书感慨地说:“使饱孤老拳,中君毒手,二人及早绝交,萚石集中,或可省去数首恶诗耶。”(钱钟书《谈艺录》卷五十四)
试图用统计数据分出诗人高低的远不止一个郭沫若。香港的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出了厚厚的两本书:《唐诗排行榜》(王兆鹏、邵大为、张静和唐元著)和《宋词排行榜》(王兆鹏、郁玉英和郭红欣著)。作者以历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点评次数、当代研究文章篇数、文学史录入次数和互联网链接文章篇数为依据,计算每首唐诗宋词的综合分值,依得分高低排出前100名的唐诗和宋词。
唐诗排名前五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和杜甫的《登岳阳楼》。在前100首中,杜甫的诗占17首,王维占10首,李白占9首,三人占去排行榜的36席。所谓“诗圣”“诗仙”“诗佛”这几个头衔真不是浪得虚名。杜甫的名篇数几乎是李白的两倍,这足以说明杜甫在历代文人和诗歌爱好者中得到的关注度要明显高出李白。
宋词排行榜的前五名分别是: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百首宋词名篇为30位词人所作,篇数排名前几位的有:周邦彦15首,辛弃疾12首,苏轼11首,李清照10首,姜夔7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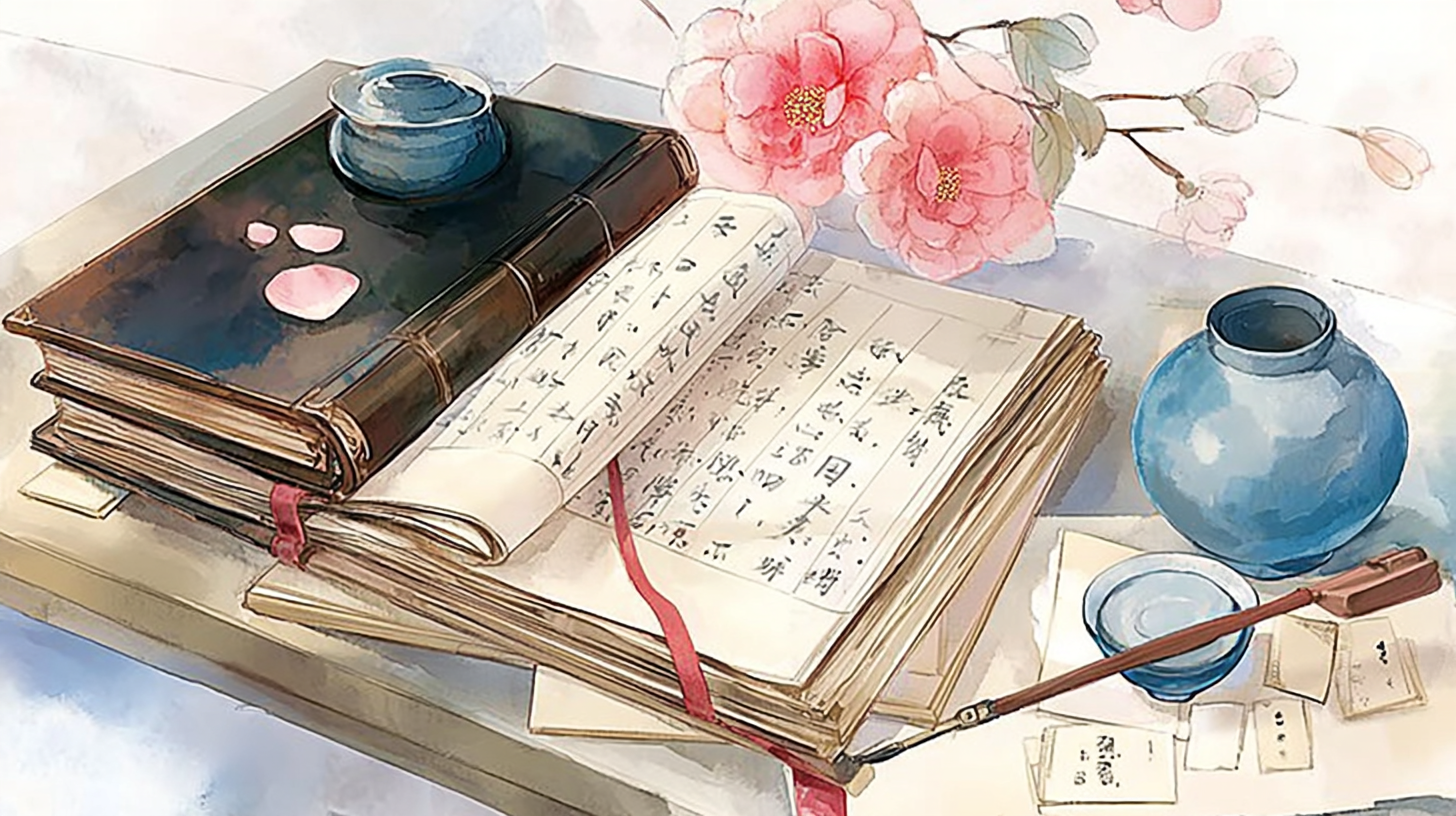
周邦彦虽然入选的篇数最多,但排名最靠前的一首才排第19位。前10首中苏轼和辛弃疾的各占两首,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李清照留下来的词作一共不过40多首,却有10首进入百大排行榜,精品率差不多是1:4,可谓极高(相比之下,辛为12:629,苏为11:378)。
唐代诗人中王之涣和张若虚也是精品率超高。王之涣存诗共6首,有2首进入前10;张若虚存诗仅2首,《春江花月夜》被誉为“孤篇压全唐”。
这两份排行榜的作者还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近现代人和古人对诗词好坏的偏好有显著的区别。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今差不多是无人不知。而这首诗在古代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很小,选家基本不选,诗评家也不予理会。
这两本书还只是用最简单的统计方法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排序。另外几位大学会计学和经济学教授(你看,会计学教授不务正业的大有人在!)用唐诗和唐代官员的量化数据验证了作诗与做人做事的关系(陈冬华、李真、杨贤和俞俊利:“诗歌、道德与治理:基于唐代科举的量化历史实证研究”,载《文学研究》2017年第一期)。
他们的研究想证明中国古代诗人的作诗造诣和诗人的道德品质是否有正相关关系。为此,他们首先需要构造诗人作诗造诣的量化指标——他们的做法是把唐代官员的诗歌水平分为三个档次:入选《唐诗三百首》的为一等,诗人在《新唐书》中被明确为进士出身的属二等(因为进士考试中有诗赋方面的内容),非进士出身的为三等。
道德水平的计量则采用史书(如《新唐书》《唐登科记》《旧唐书》等)对这些人的描述用词,凡用上“忠诚”“仁义”“功德”“信礼““正直”一类词汇的归为品德高尚。反之,凡用上诸如“奸佞”“贪腐”“谗陷”“曲附”“忿狷”一类词汇的则视为品德低下。
作者构建了一个回归模型,仔细甄选了样本,控制了环境因素,最后得出结论:诗歌造诣越高的诗人,品德也越高。四位作者中有三位都是我熟识的老朋友,尽管我认同这项研究的认真和可靠,但对诗人是否因为道德高尚而适合担当治理责任却高度存疑。诗人一般而言浪漫而率性,热情奔放但情绪多变,喜欢仰望天空,不善脚踏实地,坐上大位未必能胜任,李后主便是很好的例子。
04
旧体诗的爱恨情仇
民国时期的文人大多是能写诗也喜欢谈诗的,尤其是旧体诗。民国诗人中,写作最勤、声誉最隆的应该要算郁达夫了。郁达夫才气高,感情也丰富,而且名士做派十足。他自己也承认,“我本逢场聊作戏,可怜误了多情你”,“佯狂难免假成真”。
有妇之夫的郁达夫毫无顾忌地疯狂追求王映霞,从热恋到结婚,感情之炽烈轰动一时。看看他那时写给王的诗:“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郁王二人1927年结婚,1936年郁达夫在杭州建成“风雨茅庐”,但不久就开始闹婚变了。至于婚变原因,夫妻二人各执一词,外人难辨谁是谁非。这时,郁达夫写下了著名的《毁家诗纪》,含20首诗,而且执意公开发表。诗是好诗,却把妻子写得十分不堪,本来还有救的婚姻和家庭算是彻底毁了。
民国文人轰轰烈烈写诗追求的还有一例,就是名教授吴宓对毛彦文的狂轰滥炸。毛彦文是吴宓熟识的朋友,也是其妻陈心一的闺蜜。吴宓和陈心一育有三个子女,看上去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谁知吴宓发现自己不可药救地爱上了毛彦文,于是公开发表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毛彦文尴尬不已,但不为所动,转身嫁给了年已65岁的前北洋总理熊希龄。得知婚讯的吴宓肝肠寸断,一连赋诗38首,表达自己的痛苦和凄凉。如果吴宓不会写诗,无法发泄自己的痛苦,估计是要跳楼的。写诗居然有这等好处,实在值得推广。

诗人被后人记住,往往不是因为某首诗,而是诗中的某一警句。民国才子袁克文写过很多诗,少有能被人记住的,但他当年劝谕其父袁世凯不可称帝的两句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却打动了很多人。
郁达夫写了这么多诗,自己最得意,也经常挥毫书赠朋友的还是一幅诗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害美人”,颇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唐代诗人杨凭的一位表弟窃用其诗篇登进士第,杨凭得知后大发脾气,责问他说:“一一鹤声飞上天”句还在吗?表弟回答说:我知老兄最爱此句,所以不敢奉偷。杨凭的怒气这才缓和了些,说:“犹可恕也。”(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引自轻言《历代诗话小品》)。
唐朝诗人赵嘏并不出名,但他的“长笛一声人倚楼”诗句却不同凡响,为他赢得了“赵倚楼”的美名。
警句的出彩常常到了“有句而无篇”的地步,甚至到了为夺句而谋命的程度。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一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名句,据《唐才子传》记载,他舅舅宋之问为夺此诗而杀了自己的亲外甥。其实,宋之问夺诗杀人仅是传言,但因为宋之问的人品实在太差,历代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相信这一传言为真。
十大元帅中陈毅和叶剑英都以擅长作诗闻名。其实,朱德和刘伯承都善写诗,且都有不少诗作传世,只不过诗名不如陈、叶二位为人所知罢了。陈毅一句著名的调侃“在元帅这边我说我是诗人,在诗人那边我说我是元帅,靠着这招两边都接受了”,让他诗名更盛。但陈毅写的基本都是新诗,在格律上不受约束。
写律诗更擅长的还是叶剑英,他的《远望》和《八十书怀》被人称道,“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读来就有老骥伏枥的奋进感。还有一首很幽默的词据说也出自他手:
调笑令·会场素描
叶剑英
头重,头重,
四个小时听众。
腰斜眼倦肠饥,
左手频看时计。
时计,时计,
有点猿心马意。
其文笔妙趣横生,经常开会的人读了很难不产生共鸣。只是我找不到这首词的出处,有识者请告我。
05
新诗之风
在近代诗方面,三联出版社2016年曾出版过一本很特别的书《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作者是日本人木山英雄。
胡风、聂绀弩、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等十余位旧文人,在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命运多舛,一点怨恨和不安只能用诗词唱和来婉转表达。木山英雄抓住这一视角探讨中国文人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境遇,读来不免让人感慨万千。其中非常含蓄的一句“把他们当作单纯的‘受害者’也未必正确”道出了历史的酸楚。受害者也往往是落井下石的人。幸好,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五四运动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也带来了新文化的各种尝试。于是,新诗便应运而生。为新诗破茧的是胡适,有所成就的却是郭沫若、徐志摩、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等人。我们来看一看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蝴蝶》(原名《朋友》,引自《梁羽生妙评民国诗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读来味淡如水,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反正是读着读着就产生妄念:这种诗我也会写呀。或许,胡博士的本意就是想让没有诗才的人一读就蠢蠢欲动。
胡适是白话诗开风气的领头人,他的诗今天已经没有人读了。新诗作者中时至今日还有相当影响力的我觉得就是徐志摩了。
徐志摩最出名的是《再别康桥》。诗共六节,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里现在还设立了《再别康桥》的诗碑,专供中国人来朝圣。我去剑桥大学时也未能免俗,转弯抹角找过去瞻仰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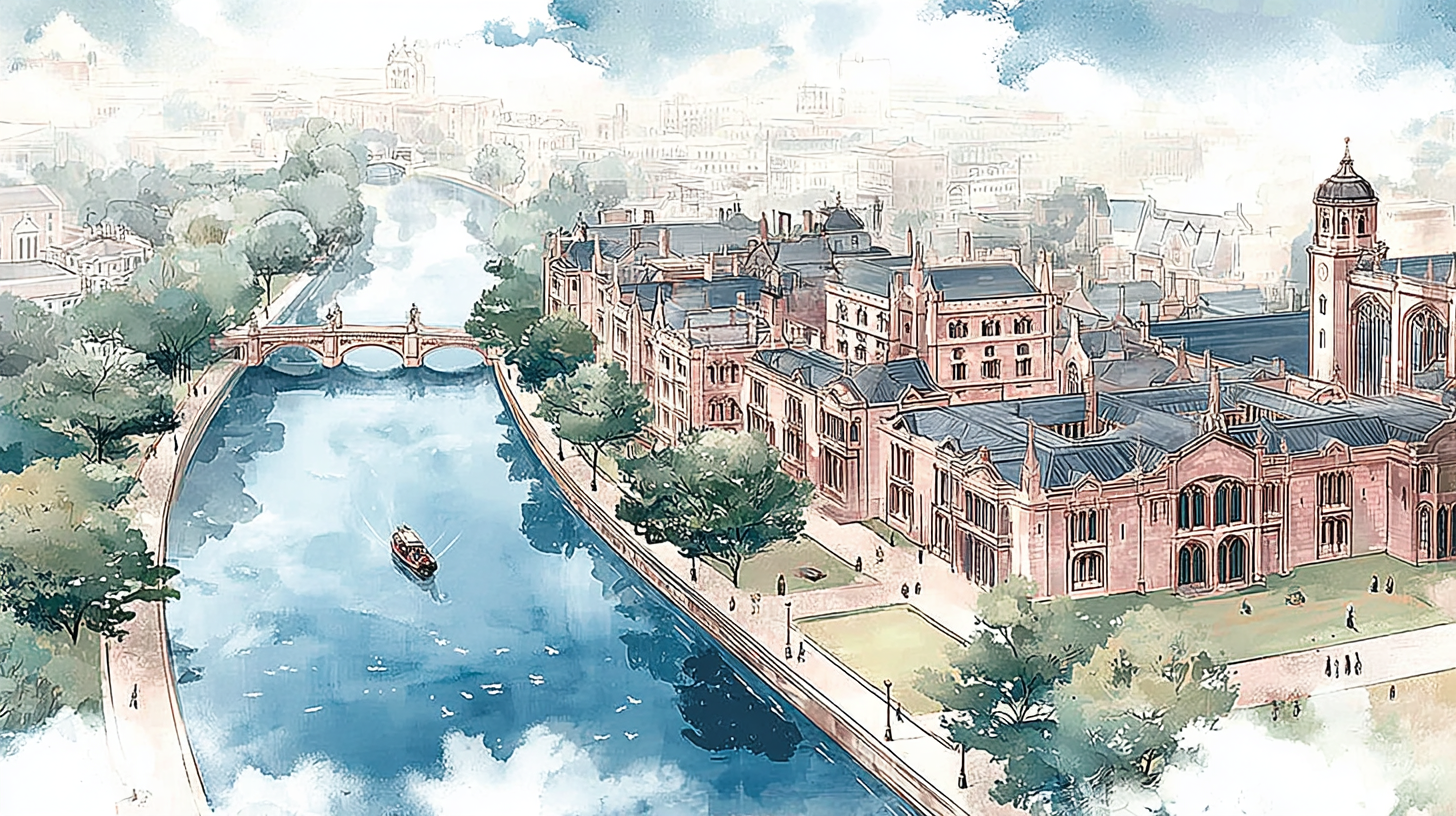
五四运动后新诗热闹了一阵,后继乏力,新诗慢慢沉寂。没想到20世纪80年代新诗再次掀起高潮,出现了四大诗人:北岛、海子、顾城和舒婷。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及舒婷的朦胧诗《致橡树》都是激励过那一代人的名作名句,伴随着一代人的青春长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除此之外,还有海峡对岸的余光中,90年代在大学生中还流行过读汪国真。
06
趣说打油诗
打油诗是格律诗一个有趣的变种。打油诗的始作俑者据说是唐人张打油,他的《咏雪》(一说为张孜所写)一诗开创了一种新的诗风:“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所谓打油诗,基本特点是不拘格律但押韵,用词俚俗,语调轻松幽默。如果严格按照这一标准,近世的许多所谓“旧体诗”也接近打油。以写大量旧体诗闻名的聂绀弩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线殊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引自高旅为聂绀弩诗集《三草》所写的序言)。
由此可知,含有打油成分的旧体格律诗其实也是诗词现代化的一个体现,通俗而易上口的“松散”格律诗可能是延续格律诗生命的一条康庄大道。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钱钟书和聂绀弩,前者是对历代诗词深有研究,写诗格调高雅、用词精准、深邃华美;后者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所作的诗极少用典,通俗而富于趣味。二者各有自己的喜爱追随者,但人数上一定是读聂诗的多,让人能记住的也一定是聂诗。
比如聂写伐木的“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又比如他描写女乘务员的“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皆轻松易记。黄苗子写书,很自然地引用了聂绀弩的诗句:“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聂绀弩的旧体诗得到的好评远超同时代其他著名诗人,其中的道理很值得我们思索。
当然,钱钟书也有趣味盎然的诗作,如这首题为《予不好茶酒而好鱼肉戏作解嘲》的早年诗作:
富言山谷赣茶客,刘斥杜陵唐酒徒。
有酒无肴真是寡,倘茶遇酪岂非奴。
居然食相偏宜肉,怅绝归心半为鲈。
道胜能肥何必俗,未甘饭颗笑形模。
首句用了两个典故:北宋宰相富弼嘲笑黄庭坚(山谷)只是一位来自江西的茶客;明代才子刘建反对学子作诗,嘲讽杜甫不过是一个酒徒。我等俗人,差不多也是好吃鱼肉之徒,对这样有趣的诗当然是心领神会。
写诗可以打油,但切忌写成“薛蟠体。”薛蟠是《红楼梦》中人物,典型的混混。他在小说第二十八回中在酒宴中为行酒令作诗,低俗到不堪入目,于是留下这么一个诗歌类别。简单说,薛蟠体的特点就是语言浅显,内容直白,主题低俗,格调下流。写诗的人谁也不想被人说是薛蟠体。

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经学家和诗人王闿运收齐白石为徒,当日在日记中写道:“齐璜拜门,以文诗为贽,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王闿运的苛评传出去后,齐白石的诗一生都无法摆脱“薛蟠体”的恶名,对他很不公正。其实,齐白石的诗很类似后来的聂绀弩,清新而不落俗套,与穷酸文人格格不入,不受他们待见也不奇怪。
诗史留名,可以是李白,也可以是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两句诗直让汪伦的知名度大大超过许多孜孜求名的大小诗人。作诗作到李白、杜甫的高度,难;交朋友交到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也难,但好像难度要低一点。
作不了诗又想蹭点诗人余光的,不妨多交诗人朋友,特别是肯把你写进诗的诗人朋友。你有好诗人可以介绍吗?









